

在高二的时候,我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。
我不是普通的高校生,而是一名艺考生。我就像所有的美术生一样:敏感,多思,焦虑。
一方面,繁重的课程令我喘不过气,我没有优等生的天赋和努力,只能时时刻刻追逐着课程进度;另一方面,我父母也结束了长达几年的争吵和冷战,他们终于决定离婚。
在这种情况下,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提出了抗议:我常常在夜里哭起来,睡眠对于我都像一种折磨。我把自己裹在被子里,感觉风扇下的空气压抑而窒息,几乎要把我扼死。夜里失眠使我迅速地消瘦,从一百多斤瘦到八十斤,几乎能看见骨头。
休月假的时候我妈带着我去了杭州的九院,诊断结果为重度抑郁。医生建议我离开画室一段时间,在家里吃药、恢复。
吃药的生活并没有能让我更好:吃了药使我昏昏欲睡,如同一具行尸走肉。我时常胃疼,这是在画室遗留的毛病。但是我不想做饭、不想点外卖、不想吃东西。生活对于我来说是件很难的事情。
我爸搬去了另一个城市,但是在走之前他来见了我一面,手里提着个笼子,笼子里有只猫。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“队长”。

队长是一只一岁半的公猫,黑色的,肚皮和爪子是白色的我爸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,这是我妈对他的评价。一个“务正业”的父亲在看抑郁症女儿的时候,不会带着一只猫来。
我妈脸色瞬间就沉下来了:“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,我又没时间,你还让她养猫?”
我听说有人会通过宠物帮助自己治疗抑郁症,但是我爸显然并不知道这些东西,他只是想“给我找个乐子”。
但是我有些着迷地盯着那只猫看。他在笼子里焦躁地走圈,用琥珀色的眼睛看着我,眼里有猫科动物干净而骄傲的神采。
我很小的时候幻想过自己会有一只猫,黑色的,就像女巫养的猫一样。猫这种生物独立、神秘而自由,和颓废又软弱的我完全不一样。
我和我妈说:“我想养,留着吧。”

队长在家里的前几天蜷缩在沙发下面,对新的环境陌生又警惕。
我原本以为这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会持续很久,因为我并不擅长讨小动物喜欢。但是当我有一天躺在床上的时候,我看见了黑色的一团——队长坐在我的床头,用它的眼睛盯着我,表情有点严肃、有点好奇。
我的心里升起了一点儿奇妙的感觉,这种感觉使我破天荒地摆脱了起床时的烦躁和低落:这只猫科动物轻易地踏进了我的私人空间。我在家始终是孤独的,但是我现在有只猫了。
我伸出手去摸摸队长的头,队长弹动了一下耳朵,任由我以不舒服的姿势抚摸他。
有队长的时候,我感觉自己更像一个正常人:我得从床上起来,跋涉到阳台上去倒猫粮;我得清理他的洗手间;我得收获他的小麦苗;我得陪他午睡;我得和他玩耍一会儿……还有最重要的,我得活着,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照顾我的猫。他对我来说是一种责任。
队长是个很好的朋友。他不会侵犯我的隐私,不会要求我“好起来”、“振作点”。在他眼里莫名哭泣、定时服药的我和别的人类并没有什么不一样

也有不那么顺利的时候。我的病情反复得很厉害,有时候脑子里的声音不停地在否定自己:你不行的,你撑不下去,你只是在苟延残喘。
有一天我坐在窗台上,看着楼下的车流和人流,突然有一阵冲动让我跳下去:跳下去,一切就解脱了,我只会给家人带来麻烦,离开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是更好的选择。
我鬼迷心窍、就将要打开窗子了。突然,队长跳上了窗台,弓着背挡在我和窗户之间,发出了大声的嘶哈声。
我啊地一声掉下了窗台,膝盖撞在地面上。疼痛惊醒了我,我仿佛拨开了一层雾、回到了现实生活中。我抱着队长,坐在地板上号啕大哭。我的眼泪胡乱地蹭在队长热乎乎、毛茸茸的身体上,他任由我抱着,就好像知道我的后怕、懊悔,也能读懂我的恐惧。
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:队长救了我的命。

如今我已经大三,在一所不出名的大学。我几乎已经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。在周末,我会回到家里,和已经是一只老猫的队长玩一会,或是陪他静静地坐着。
长有没有治好我的抑郁?我不清楚,因为药物和心理治疗也起到了莫大的帮助,但是队长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——他救过我一命、给了我牵挂,让我能“以为自己是个正常人”一样活下去。
我将永远爱他、永远感激他。

动物干预疗法,是抑郁症的一种辅助疗法。早在18世纪,就已有疗养院采用小动物作为医疗辅助手段。已有研究表明显示,动物辅助疗法可以治疗抑郁、焦虑、孤独症、行为障碍等心理疾病。
由于动物对人是“无期望、无要求、不加掩饰”的,因此患者可以在动物面前表现得轻松自然,敞开心扉。动物是患者宝贵心理支持来源,可以使人感到温暖、被喜爱、被需要。而饲养动物的过程也可以为患者培养责任感,以及增强自尊。
在家庭中,宠物也是常见的支持来源。他们就像最忠诚的骑士,会带给我们长久的陪伴和爱。

心理咨询师推荐:乐天主任咨询师 周逸珠
作者 | 周鑫畅
编辑 | 徐佳茜
策划 | 吴乐东
上海心理咨询中心原创文章,版权所有,转载请写明来源以及网站链接,违者必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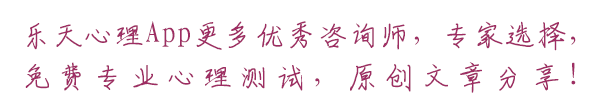
◎欢迎参与讨论,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、交流您的观点。
 上海乐天心理咨询中心是上海心理咨询机构,强迫症、抑郁症、青少年心理咨询、婚姻家庭咨询等心理咨询服务创优全国
心理咨询中心地址: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2240号鼎力创意园B401室 免费预约电话:021-52951186 021-37702979
Copyright © 乐天心理咨询中心 www.wzright.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10044013 -4号
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403号
上海乐天心理咨询中心是上海心理咨询机构,强迫症、抑郁症、青少年心理咨询、婚姻家庭咨询等心理咨询服务创优全国
心理咨询中心地址: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2240号鼎力创意园B401室 免费预约电话:021-52951186 021-37702979
Copyright © 乐天心理咨询中心 www.wzright.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10044013 -4号
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403号